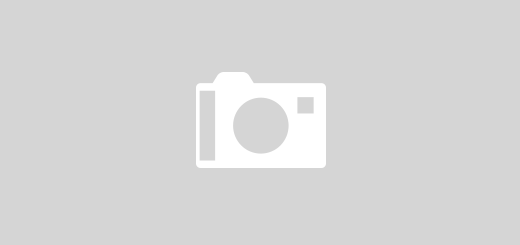分享日记|■向天笑乡土诗……
![]()
■村庄
任何一个村庄都有两个村庄
山上的村庄
是祖先挨着祖先
山下的村庄
是晚辈跟着晚辈
如果不是逢年过节
不是有人要安葬
山下的总是忘记了山上
任何一个村庄都有两个村庄
山下的人总想离开村庄
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闯荡
山上的人虽然相安无事
但在地盘上却是寸步不让
其实,所有的人走来走去
走一生的时光
只不过是从山下走到山上
任何一个村庄都有两个村庄
一样的泪水流着两样的目光
山下的总在上升
山上的总在下降
●草帽
一根草的力量是弱小的
轻易地就可以扯断她
当她们互相勾结起来
从顶端,一圈一圈地扩大
就可以遮天蔽日了
就可以站在你的头顶上
为所欲为了
让你活在她的阴影里
●远方的绵羊
你信不信,一个女人的枕头是一座山
她在孤独中把思念变成一只只洁白的绵羊
在寂寞里又把绵羊一只一只地赶上山岗
九只、九百九十只、一千九百九十九只绵羊
在泪水无声的滚落中无望地前进
赶到最后一只绵羊时,那个牧羊人还没有出现
只有她一人静静地坐在山顶上
无助地看着那些绵羊冲下山岗
没有一只绵羊愿意陪伴在她的身旁
她耐心地守候在那里,直到变成一只绵羊
在她的眼里,离去的绵羊变成了兔子
一只一只地抽打,直到满腹的思念变成怨恨
●冰冻的声音
下雪了,贫穷的孩子堆积雪人
不如意的,可以随手捣毁
全部的快乐在于堆积与捣毁之间
偶尔停下来,听雪人那冰冻的声音
孩子与孩子之间在较量
雪人与雪人之间在交谈
它们传递着纯粹的思想
宁静的阳光落在雪地上,像刀刃
孩子们都感到不可思议
为什么先堆积的后消融
后堆积的反而先消融
一觉醒来,雪人不见了
那些胡子、眉毛还在
那些冻僵的忧伤还在
●飞鹅山下的舅舅
冬天的风,在飞鹅山下冷冷地吹
你已经没有感觉,你比还风还冷
我带着鲜花来到你的面前
你张着嘴,说不出一句话
我轻轻地抚摸着你,舅舅
你的眼闭上了,嘴也闭上了
你像平时一样讲究,衣冠楚楚
不过,今天从内到外都是新衣
你安安静静地睡着,睡着
你的微笑被塞进像框
那些被泪水打湿的声音
流成河了,你也不回到岸边走走
还有三天就要过年了
春风正在远方朝飞鹅山吹来
吹绿将为你建造居所的山顶
●路的尽头就是家
昨夜我梦见了你在遥远的地方呼唤我
你站在青青的河边草深处
你不动,春天也放慢了脚步
直到月亮从湖上升起,你还是不动
我不知道你在等候谁,花那长的时间
青草也会枯黄,你穿着黑色的长裙
面前躺着一条漫漫的黑色长路
天空飘满了雪花,那是一个人的泪
最后,我们到达了我的老家,一个很小的村庄
我的父亲在寒风中站成了一盏灯,在温暖的梦里
你依偎着我,不再前行了,路到家了就到了尽头
为什么我们花了如此之久才明白路的尽头就是家
所有的奔波都失去了意义,我们停留在某处不动
守护着我们曾经的青春年少,忘记了还有衰老
●教堂外的阳光
像泼洒在地的水,亮晶晶的
河水一样荡漾的阳光荡漾在教堂的周围
远处,麦绿的麦地上
我的母亲正朝教堂生气勃勃地走来
把自己的后半生交付给十字架
交付给异国他乡的耶稣
仅仅认得自己名字的母亲
抱着厚厚的《圣经》行走周末的路上
从没有见过的神啊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左右了我的母亲
让她幸福地在教堂里忙碌着
我每次远游带给她的礼物就是十字架
那比什么都珍贵
在阳光下,闪耀着耶稣到来的光芒
●谛听母亲的声音
啪哒,啪哒
母亲在槌打一件棉衣
哦,那当时觉得单调、乏味的声音
如今像潮水一样涌来
久久回荡,迟迟不肯离去
那样悠然、自在的声音
就像提速的火车,在夜间的大地上穿行
除了声音,还是声音
哦,我屏住呼吸,在池塘边
在母亲曾经捣衣的池塘边
那冻红的手,挥舞着木槌
在冰窟之上,不停地敲打、敲打
但如今,还是夏天
她的身影就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再也听不到那从容不迫、举重若轻的声音
啪哒,啪哒
●等待母亲落气
五月,最后一场大雨
落在早晨的朱家庄
我站在母亲的病床前
等待等了我十天的母亲落气
姨、姨、姨
在我一声声的呼唤里
母亲久久不动的头,轻轻动了一下
就永远停止了呼吸
我让妹妹用屋前的栀子花
扎了一只别致的花圈
满房飘散着淡淡的芳香
我满脸泪水呆呆地站着
母亲的表情极为安详
安详得像要随时复活一样
●父亲成了落伍的砌匠
父亲,一生不知砌过多少房屋
只是亲手盖起的成了他人新居
自己出身不好,只搭一间别厝遮风挡雨
沉甸甸的砖头像沉甸甸的痛苦
捏在手里不知道是怎样的把握
每一次新屋落成的喜酒
喝下去,是满腹的委屈
再勤劳,也有不能致富的时候
再贫穷,也有翻天复地的时候
当父亲老了,儿子在老宅基地上建造新居
没想到收藏多年的砌刀与泥桶
在自己的地盘上却派不上用场
他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端茶送水
仿佛对帮忙的乡亲把幸福送上
电灯电话楼上楼下不再是什么神话
城里的孙子,一句想他
像温暖的阳光落在雪花
就把他一生的悲伤融化
●飞蛾
一点光亮,就可以打开你的翅膀
一点光亮,就成了你飞翔的方向
你明知越是明亮的地方
越是危险的地方
但你不会呆在黑暗里、呆在寂寞里
你要透明的生活,你要燃烧自己
明知灯火会成为你的葬身之地
你依然张开柔弱的翅膀,坚强地扇动
宁愿满身是伤,伤痛自己
也要完成,最后的、完美的,飞行
那优美的姿势,停留在记忆里
弱小的,总是能打动坚强的
火焰也为这顽强的生命跳动
飞蛾不在了,火焰也会慢慢熄灭
■麦子
总在清明节前走近麦子的身旁
从麦地到麦地,中间除了坟地
还有金黄的油菜地像飘浮的船一样
还有灿烂的蝴蝶,在翩翩飞翔
劳动是一种飞翔
祭祀也是一种飞翔
从种子到麦子,除了劳动
还是劳动,抽穗的是希望
我的儿子站在高高的山岗
他说乡村像油画一样
他说中国的麦子在南方
牵着祖父的手看起伏的麦浪
他说这里的空气真香
■当年那个长头发的女孩
一些当时并不知道是美丽的美丽
到现在,早已彻底消亡
消亡的不只是她的一头长发
还有青春、热血与梦想
那苦难的岁月,她甩一甩头
就成了幸福的时光
那鼓励的眼神像刚刚升起的太阳
总是闪耀在她微笑的脸庞
如今,在回乡的途中偶尔相遇
蠕动的嘴唇有一种交谈的渴望
最终什么都没说
笑了笑,路过我的身旁
只是抚一抚齐耳的短发
一副很知足也很满足的模样
那少女时要与我一同飞翔的梦想
变成洒在她身后的落叶与阳光
那至少要早苍老十岁的背影
像一盏灯,一盏赶夜路的灯
把我的黑暗和幸福全部照亮
与她比起来,算得了什么
那些生活在城里的不快与忧伤
■想念我的乡村
一天逝去又一天过来
拥抱我的是一种莫名的情怀
总想到乡下去走一走、坐一坐
看看老家门前的栀子花是否绽开
每一条田塍,每一座山头
童年的影子还在荡去晃来
尽管小黑狗、老黄牛不认识我
但宁静的幸福还是扑面而来
任何一个女人也唤不起
我对她像对家乡一样的热爱
站在家门口我不要半点风采
再没有什么思念
比归乡的路还长、还长
还要偏僻、还要深入、还要期待
●草鞋
最艰难、最困苦的日子
汗水与泪水相伴的日子
草鞋,一双早已破旧的草鞋
绑着我的赤脚,行走在乡村
行走在那些看不到出路的日子里
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
我会从狭窄的田塍走到宽敞的街道
从矮小的别厝住进高楼大厦
草鞋,像我儿时就早亡的伙伴
常常走进我半夜惊醒的梦里
●孤独的狼
半夜三更,雪亮,无处可归的狼
在弥漫的雪花中停滞不前,总在原地打转
刨雪,咬雪,深入冰冷的陷阱,不能自拨
一堆雪,一堆丰满的雪,像羔羊蹲在面前
更像一堆饥饿,眼睛点灯了
再没有隐蔽的角落
忍不住嗥叫,在遍野的宁静里
粗暴的声音,回荡得如此之久
只有满天的星星像泪珠一样闪亮
眼里灯火渐渐熄灭,嗥叫声渐渐减弱
除了雪花,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其它的花朵
雄起变得虚弱,热情在寒冷中飘散
早已变得雪白的狼,完全静止不动
远远看去像羔羊一样
只有风吹过,这无边的宁静
■在田野里鞠躬的父亲
他一生只掌握着锄头的把柄
连猪尾巴似的小辫子也抓不住
直到蚯蚓般的皱纹爬上脸庞
我的父亲,依旧在田野里鞠躬
鞭子捏在手上,只是做个样子
谁能听懂牛的叹息,除了他
汗水早已取代了泪水
他的心目中除了庄稼,还是庄稼
在那些充满硝烟的批斗会场上
就是石磙压在身上
他也不会随便放出一句话来
只有当他的双脚踩在泥土之上
把月亮像草帽一样戴在头顶
他才会如同落难的皇帝,重返故宫
■光头大伯
从我看见他时
就有颗闪亮的头颅
搁在他的脖子上
很多年前,又仿佛在眼前
他还在田间专注地劳动
阳光伸出温暖的手
抚摸田野,也抚摸他的光头
在这过程之中
水稻显得无比成熟
如懂事的儿女
紧紧围绕在他的身旁
虽说他早就不在了
可这么多年来,还有一颗闪亮的头颅
晃动在家乡的田野上
■喜拉二胡的叔父
竹子、蛇皮、马尾、松脂
制造了我叔父一生的欢乐与悲哀
村长的夫人也曾奔音乐而来
奔得叔父遍体鳞伤
在庄家湖畔的鸭棚
他把二胡拉给一群鸭子听
在阳新赤马山矿区
他站在山溪里拉给鹅卵石听
他喜欢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山岗
看满地的麦苗被风吹动
遍野的音乐,归他一个拥有
晚年病重,他让人把床搬到窗前
把二胡摆在旁边,听窗外的竹林弹唱
叔父的二胡哑寂了,四川来的婶子也走了
2005/11/6
■流干泪水的村妇
她的美貌,被岁月剥削了
在洗衣与洗碗之中
在插秧与割谷之中
她仿佛忘记躲在草垛里的梦想
塘水、田水、井水,甚至雨水
淹没了她的青春、她的激情
在哭嫁与哭丧之中,陪伴别人
流干了属于自己的泪水
把希望寄托在丈夫和孩子身上
把艰难的日子缝缝补补
把道听途说当作重大新闻传播
从来没有鸡蛋碰石头的***
偶尔上一回街,就像过了一个节日
还在镜子前,精心梳理一下自己
■下雪
我的父亲能听到雪花落地的声音
我在这个日子回到他的身边
宁静、温柔,没有飞扬的尘土
一堆柴火,就是一个温暖的家
哦!这最美的时间与空间
父子俩都不敢惊动,火焰
伸出舌苔,轻轻地诉说
多么洁白、纯净的世界
只有我的村庄,我的家园
在它的面前苦难微不足道
下雪了,雪还在下
淹没了我奔波多年的旅程
可父亲的目光踩下深深的脚印
从我的心上一直踩到家门口
■芦花鸡
■一场瘟疫过后全村都没一只鸡了
是一个江西老表将你和你的同伴
卖到我们家,我看见你长得与众不同
一身漂亮的芦花,于是要单独喂养你
每晚给你洗脚,让你在我床上睡觉
长大后,你的翅膀硬了
天天送我到校门口,就是放学
你还能准时到村对面的山岗来接我
那年春节前,趁我熟睡父亲抱走了你
你也不叫醒我,就那样被出卖了
换来几斤过年的猪肉,换来我对贫穷的理解
我的父亲年迈了,直到现在
他从不吃鸡肉,也不喝鸡汤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除了我
2005/11/6
■老黄牛
老黄牛极度冷静,在田野
在收割过后的田野
悠闲地踱步,审视
暖融融的阳光披满一身
在它轻微的喘息里
已走到了生命的边缘
泪水汪汪地望着多情的主人
还带着微笑的模样,让人心寒
它不停地回头,张望,倾听
仿佛田野传来庄稼拔节的声音
它一步步地走动,留下最后的足迹
若干年后,在一家餐馆里
一头牛,从火锅里站起来
唤着我的乳名,让我惊愕万分
■玩泥巴的孩子
泥巴是世界上最廉价的玩具
比变形金刚更变化无穷
猪、马、牛、刀、枪、笔……
万事万物,都在拿捏之中
我像玩泥巴的孩子,搬弄方言土语
只怕俨然大人一样的批评家
一脚就可以捣毁我全部的心血
没有谁知道这也是发明、创造
在商品与钞票之间,保持一颗童心
永不贩卖这些泥巴玩具
也不指望别人摆在案头
我只不过像那些泥巴玩具
在暴雨来临之前
趁机歌唱
■泥土
陶罐、瓷碗以及坛钵
显得极为纯洁而圆滑
这些来自泥土的东西
遮掩本来的面目陪伴着我们
在雨水和阳光之中
一些泥土长出一茬又茬的庄稼
还有一些泥土,在柔嫩的火焰中
变成了坚硬的青砖红瓦
用来建筑我们的村庄
当我们在生活中力不从心
一些泥土还会镀上金色的光泽
成为法力无边的菩萨
劝我们回头是岸
也许还没有回到岸边
一些平时从不动用的泥土
在花圈和泪水之下
成为我们最后的居所
■棉花
棉花柔嫩地绽开
如皎洁的月亮,雾状的光芒
笼罩着整个村庄
并将我少年的往事,照亮
没有棉袄和棉裤穿的冬天
寒风挥动无数的刀刃
在我的周围闪闪发光
只有课本的铅字
燃起一堆堆篝火
温暖我的心房
偶尔抬起头来,望见天上的白云
有如柔嫩的棉花,静静地飘荡
现在走进秋天的田野
棉花,伸手可及
温暖,也伸手可及
■怀念田野
多年了,田塍如温柔的手掌
抚摸着我旷野一样宽广的思念
那些思念,已长出金黄的麦穗
涌动之上,漂泊着父亲的背影
涌动之下,埋葬着祖母的骨灰
惟一的空隙,就是我走过的道路
那道路的尽头,站立着的稻草人
神气十足地穿着我丢弃的衣裳
至今还在站在那里守望
一只鸟,飞过
无数只鸟,跟着飞过
■乡村的灯
乡村的灯,照亮着我一生的背景
恬静,温暖,像身影一样晃动
我的村庄,活在我的心上
桐籽灯、煤油灯
盏盏点亮我的童年
星星点灯,点亮少年的心头
电灯、电话不再是神话
楼上楼下的乡村
依旧在萤火灯的飞舞中沉睡
只有月亮才是乡村永远的灯
2005/11/11
●放牛的伙伴
放牛的伙伴,当初三三两两
现在还是三三两两
只是当初在同一个村庄
现在却天各一方
有的早已死去,在冬天的藕塘
有的成为富翁,奔驰在高速公路上
他的方向盘始终没有朝乡村这边打来
他前方的道路远比田塍更宽广
是谁把我们儿时的几个伙伴
常常想起,我多年没有见到你
却把你的相片揣在在身上
像揣一堆儿时的篝火
在寂寞时,一个人独自点亮
也许照不到你的远方
2005/11/11
●那只山鹰
再强健的翅膀
也有折断的时候
那只山鹰,我平时只能仰望的山鹰
就这样停落在我的家门前
一群鸡
往日见它就到处逃窜的鸡
正在围攻它
没有威严,也没有庄严了
那只山鹰,可怜的目光里
充满逃生的欲望
内心的伤口比翅膀更加血淋淋
我把它关在另外一个笼子里
第二天早上醒来,它再也没有醒来
它的灵魂不许它在低处行走
2005/11/11
●拴在树下的童年
我的童年,拴在家门前
一棵红枣树下,那一块小小的树荫
就是我活动的全部天地
那时我多想有一双麻雀的翅膀
从一片屋檐飞往另外一片屋檐
或者像燕子,在一栋房子里自由地出入
长大后,我见到树荫
就有一种家的感觉
树长大后把荫凉还给大地
我长大后还什么给父母呢
2005/11/11
●地嘴山
你相信土地有嘴吗
我村里的人都相信,相信了不知多少***
反正惟一的一座山就叫地嘴山
山不高,树也不大
只是用来葬人,
更多的时候用来放牛
2005/11/11

————
✅生活小常识|✅生活小窍门|✅健康小常识|✅生活小妙招✅情感口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