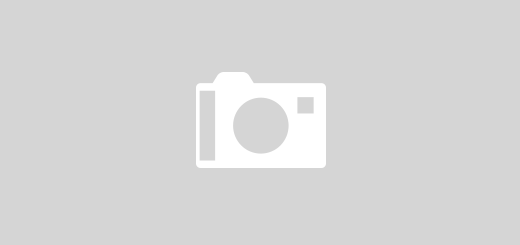分享日记|桃花筛落一片光斑———凡斯诗歌印象……
![]()
凡斯开始在构筑第三本诗集。如果写诗的过程可以一本诗选集结束一个阶段的话,那么凡斯的创作就到了第三阶段。
第一段落为《机器马》(其实包括了“机器马”之前很长的一段助跑过程,这里主要指那些较为成熟的观念诗)。在他标榜为工业主义的几组较有份量的诗篇中,留给我的印象是迷狂的尼采哲学和强硬的未来主义建筑风格与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的混合物,其将钢铁、混凝土、玻璃、性器官强制挤压、镶嵌的一种怪物而呈现出当代诗歌“丑陋”的反审美品质。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人类忙于默哀或欢呼而暂失秩序的文化荒地上,凡斯钻了个空子——就象当年海子拥有的那种特别美丽的幻觉:“秋天,王在写诗……”———其实谁也没有见过上帝的靠椅,在那种特定的情景,信手拉过身旁的一只木制椅子坐下,就有了上帝的感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人们开始大兴土木,营造长城或阿房宫,省略了孟姜女的眼泪。中国诗歌史中最近的一次创世纪体验同时又是文化人类的一次幻觉***,凡斯的《机器马》产生于这一背景,又随着这一思潮的式微变成个人的一段历史。
第二段落为《肖像》。这本集子的名字已经将一种力减少到零。象一名战后的幸存者在一片废墟中捡拾起一堆记忆的残片,整理、贴标签、存档。在一种无奈的心态下满城里打电话寻找熟悉的女子、亲朋聊天,坐落在达利的软钟表前面不失为谈情说爱的好时光,孤独时折一束花到伟人的墓前静坐,伟人们的骨水是治疗孤独症的一剂上等的药。这样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它恰恰成了许多人都曾经有过而被凡斯集中展现的白夜。
凡斯诗歌的第三阶段,目前还是一些尚待整理的手稿合在一本硬皮笔记本中,其中一些已被挑出来,最近连续在《特区晚报》副刊以组诗形式出现。这些诗以坦率闻名,坦率得令人“瞠目结舌”。凡斯诗歌因写“性”而成“被告”,凡斯无辩。我们习惯了“关关睢,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却不能习惯“你抚摸她的背从颈到脊/像抚摸一张荷叶/手感很好白光下是一层细细的毛。”我们习惯了纵的借鉴却忽略了横的比较,相对于西方文学,这种写法不过是从劳伦斯的腋下拔了一根汗毛。我们从习惯诗歌的听觉到视觉,却还没有习惯诗歌的触觉,而这一点已让魏尔仑等法国象征派诗人写腻而既成历史。今天这种辨识已毫无意义,因为《寝室的忘情叙述》在凡斯的近作中属于一种过时的表达形式。我感兴趣的是诗歌作为诗人自由存在或行为的直接叙述形态,象撕开一页纸而呈现出随意的机遇的纸边形状。凡斯在进入这种状态,我设想凡斯笔下的众多女子是同一个女子,对于同一个女子的手感却今非昔比。就如同德拉克利特说过的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众多女子的名字成了凡斯多次踏入这条河流的不同标识或符号。河水继续向前流去,而向后漂走的倩影成为凡斯诗歌蜕化剥落的一件件旧式衣衫。
凡斯的第三度写作是诗歌的形而下实验,在所有进入这一实验的诗人中凡斯似乎享有更为宽阔的当下场景,获取厕身其中的表象材料原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将这些年淹死在***城、夜总会啤酒中的影子一概打捞出来,在诗句中存活。我倒觉得《聊斋志异》中关于书生与女鬼的脚本被当代诗人拿来演绎了一遍又一遍。凡斯在泛文化体验中消解着原先的精神原核。在此之前,凡斯的诗中屡屡提及“阿尔”,可以想像这个词与他个人有着不可分割的精神关联,但是这个词现今已随便到轻易地挂在嘴边,剩了空洞的符号。梵高的向日葵、梵高的崇高在凡斯这里变得毫无意义,“阿尔”其实离凡斯很远,它至多是一粒或白或黑的棋子,被凡斯夹在中指与食指之间,思忖着放在哪一个位置才会恰当。
文本的实验已在逐渐离弃它的文化母体,离弃诗人作为生活的人某次体验中或苦或乐的表情,它象一些中性的物质,如同被反复提纯的钢水,或者无味无色的灵魂。具体到凡斯新近的一批作品,那些零落的诗句,如同抛弃太阳的光线,在桃花妖冶的颜面上,成为自由落体。我们检阅着这些纸上的铅字,与看见地面上遗落的一片光斑并无区别。

————
✅生活小常识|✅生活小窍门|✅健康小常识|✅生活小妙招✅情感口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