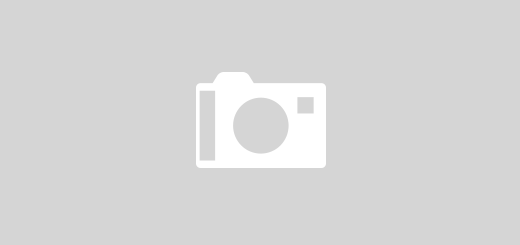分享日记|中国低诗歌系列文论之——……
![]()
中国低诗歌系列文论之——
“诗性正治”
张嘉谚
本文提出“诗性正治”这一个命题,意在探讨中国先锋诗歌总会触及到的敏感问题——诗与政治的关系。
打从心底说,本人对所谓“政治”是相当讨厌的,更不感兴趣。但几十年下来,深感政治这玩艺儿不是你想避开就避得了的。涉网以来,发现许多诗人在普遍回避政治的时候,对“政治”又未必了然,相当多的人甚至对政治缺乏起码的常识。本文不打算对这些朋友作什么政治启蒙,只想从诗性角度探讨一下“诗正治”(注意:不是“政治诗”)的问题,意在为中国诗歌当前的先锋写作清除一种心理障碍。
回避政治的耻辱
政治是诗歌绕不开的东西,却被当今中国诗人普遍回避。为什么?个中原因不外是:长期的专制高压造成了诗人普遍的政治畏惧与心理阳萎,这一点,谁也不愿承认然而又都心知肚明。或许,也有因对政治“反感”而疏远政治的吧。总之,中国诗人因回避政治之“险”与“烦”而想出了“种种奇妙的逃路”(鲁迅语),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什么第三代写作、纯诗写作、零度写作,私人写作、身体写作、口语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橡皮写作、中间代写作、70后写作、第三路写作、下半身写作,垃圾派写作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写作主张,无不煞有介事,既躲开了可怕的政治阴影,又名正言顺,还能坦然显示一份清高甚至正当地博取“先锋探索”的名声。但是,审理中国诗坛这20多年的历史,后人只看到诗人们回避极权政治的耻辱,举阳不起的懦弱以及不乏卑劣的自以为是。
作为诗人,作为文艺家,你真的回避得了“政治”么?如果把政治看作历史文化与社会文化的集中表现,民众生存其中的现实环境。我们就处处都在与政治打交道,政治也就时时刻刻将我们包围。谁也别想“此地无银三百两”,试图加以逃避。在我们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可以说“到处都是政治”。那些口口声声不谈政治的诗人或总是小心翼翼回避政治的文人,岂非像驼鸟一样把脑袋钻进沙堆自欺欺人?身处极权专制语境之中,中国诗歌要么“政治化”,即为极权政治所“消化”;要么“化政治”,以清明的诗性“教化”政治或“化解”政治,即本文倡导的“诗性正治”。舍此而行当然也可以选择“第三种诗写道路”,但若干年后回头一望,只怕大多诗写流派的身上抹不去那一块“奴化”的印记,就像诗人凡斯一首诗所描述的:醒来发现我在猪车上,变成了一只大白猪!
何谓“诗性正治”
当今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介入已经表明:研究者通常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政治性文本的,放开广阔的视角看,“政治性”即各种微观的权力机制,可说随时随地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当代西马学者弗•杰姆逊干脆这要样认为:“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弗•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由于政治权力在现实生活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中国诗歌要获得健全的发展,在随时随地都难免触动或涉及到政治的情形下,强调诗性精神之形而上与世俗政治之形而下的区别是完全必要的。弗兰西斯•庞哲谈到“诗的功能是滋养人类精神,使之从宇宙中汲取乳汁”时说:“当人类不仅仅为其特有的思想感情而骄傲,也为其能够自化并与自然融合而骄傲时,就有望获救了。”他把“希望寄托在诗歌身上”,希望借助诗歌,让“世界占领人类精神,致使其失语之后重新发明一套语言。”(《物之声》)先哲们仿佛都在异口同声地说:诗人可以发扬诗性之美与善的精神教化功能对世俗政治加以审视——这种审视,是以神圣性对治世俗性,以精神化对治物欲化。诗歌的这种审视功能,便是本文倡导的“诗性正治”。
为什么用“正治”而不用“政治”?
这是因为:“正”字,在中国古语中同“政”。“政,正也。”(《说文》)可见,“正治”并未脱离“政治”。由于“政治”一词在现代社会具有特指性,我们采用“正治”一词强调其本义与原义就极有必要了。“正”,顾名思义,除有正当、正常等涵义外,还意味着公正。所谓公正,应以三个向度作为衡量标准:一合天道,一合人心,一合地德。天道与人心不难理解,而所谓“地德”,指的是历史文化积淀而成的普世价值。这即是说,诗性正治是以“道心”为根本,以“德化”为准则的。
诗性正治可以用一句简明的话来解释,即:以诗性精神感化心灵,以诗性智慧教化世人。
因此,“正治”一语比起“政治”来,有更高更深的含义。竖向地看,“政治”强调功利性,多指向社会层面的权力性操作。“正治”则偏重诗性而进入精神性层面。如此,“正治”便因其精神内涵的丰沛性涵盖了“政治”,同时又越过现实层面,成为超越世俗政治的诗性表述。横向性地看,“正治”也在党派政治性之外包容了更多更广的文化对治意义。
“正治”一词,是“正”与“治”组合,怎样准确地理解它们呢?
“正”,在“诗性正治”这个词组里主要指“正当”与“正常”之义。“正”之本义为“匡正”。谈“正治”即有针对社会生活中一切权力关系权力机制与权力话语现象的偏差施行匡正之意。这种匡正,履行的是诗人天赋的话语职责与话语权力,针对的是人类历史发展至今的愚蠢与恶行,抨击的是人性深处的劣根与恶业!
“治”在这里主要取其“对治”或“矫治”之义,所谓“对治”与“矫治”,有发现、审视、揭露、批判、审理、清除等“针对性”含义。“正”与“治”结合为“正治”。便意味着“正常的对治”与“正当的矫治”。它未必是“正确的对治与矫治”,或者说,它不以对治或矫治的“正确”自许。对于诗性精神,正确与否不是它着意的(因为“正确”的衡量准则很难依谁认定),诗性精神关心的与其说是“问题的解决”,无宁说是“问题的提醒”。诗是性情的表现,它的作用只不过是“感化”而已,诗在精神之域,它的基本功能是“教化”而非“驯化”。
诗性正治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心态。它是激情的大悲悯与大爱心的流露与勃发,这也就意味着“责任”,诗人的责任与诗歌的责任。诗性正治的责任通过爱怒悲憎表现为许多层面,从对治自我开始逐级扩展到亲友同胞与社会,再扩大到民族、国家、人类,广阔可对应宇宙万物,收拢回来便针对自身。所谓“正治”,不光要对外部世界的不义与不公作外向性话语批判,同时还意味着针对内心污秽作内向性的清除,“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以健全和完善自我人格。比如这样的诗句——
张志新,我后悔没有把我的处男身献给你
如果我真的把我纯洁的一塌糊涂的处男身
颤颤惊惊地呈现在你丰韵犹存的***前
我想象不出你这个***者会怎样引领我
进入你神秘的阴道我会怎样的颤抖激动
在一阵伟大的冷颤后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在一个伟大的女人的阴道里我炼就了一身正气
张志新,我后悔没有把我的处男身献给你
当我颤抖着写下这行字的时候
我的生殖器已长满了冠状的尖锐湿疣
但仍然挡不住我到处嫖到处乱搞的习惯
我却不敢再有一丝丝和你性接触的念头
那怕就是握手我也不敢
我的生殖器已是一根带毒的骨头
支撑着我丑陋的灵魂
——典裘沽酒:《张志新,我后悔没有把我的处男身献给你》
诗人杨春光评点时指出,这里不仅有对“强权政治罪恶的批判”,同时也深刻触及了“现时人们心灵中需要深刻反省自己的政治懦弱与无耻道德交织在一起的综合阳痿症”。这种写法非常真实地“把真挚的美好心灵和龌龊的下意识都和盘托出,既赤裸裸地给人看,又恶狠狠地让人批判和审丑,以其自身的灵与肉的忏悔,来形象而生动地完成了对一个愚昧甚至可以说是卑鄙的无原则、无理智、无道德、无清醒、无悲鸣、无怜悯、无良知和无羞耻的民族的集体犯罪的大控诉!”
典裘沽酒此诗出自“性情”即诗性精神的真实表达,他那外向性的愤怒揭批与内向性的自我忏悔,均以诗性话语出之,使这首诗的象态话语诗性饱满且大义凛然,充满了“诗性正治”对“世俗政治”的鲜明对治性与强烈的冲击力。
由此可见,本文探讨的“诗性正治”,也可以叫“诗人正治”、“诗歌正治”、“诗化正治”、“诗学正治”、“性情正治”、“道义正治”、“精神正治”、“文化正治”等等,本文以“诗性正治”概而言之。
从更深层的意义看,诗性正治中的“诗性”,指的是“诗意化的精神性”。“诗性正治”这个概念的有机性在于:如果说,“诗性”偏重于诗人精神人格的内在修养,“正治”则偏向外向性的世俗指涉;于是,诗性正治便将“崇高”与“崇低”,“内圣”与“外王”统一于一体。一方面,“正治”是以“天道”、“人心”、“地德”为准,强调干预人类社会活动一切领域的现世关怀,另一方面,“诗性”则是以“天道”、“人心”、“地德”为本,标示其对人类精神提升活动的拥抱与理想观照。在诗性正治中,诗性为本体性建设,是为“体”;正治为实际操作,是为“用”。因此,诗性正治在实际上有很多层面。从更高的层次看,对于诗人,诗性正治是最完美的人格体现——如但丁歌德,屈原杜甫等大诗人集内圣外王于一身;对于诗歌,诗性正治也体现出最完美的品格——我们不难在历代以来的巨构杰作中找到例证。
“诗性正治”来源既久,亦将长远绵延。即使民主社会真正确立,诗性正治仍会继续更宽泛,更细化地展开对社会文化负面因素的揭露、警醒、批判与提升。
“诗性正治”与“世俗政治”
提出“正治”这一概念,可以很方便地将“诗性正治”与“世俗政治”加以区别,避免别有用心的人将诗人的“正治”与政客的“政治”混为一谈。为了真正明白什么是“诗性正治”,有必要将其与“世俗政治”(社会政治、党派政治等)作一番比较。
真正的诗人涉及政治,如屈原但丁、歌德海涅、陶潜曹植、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多半是“以性情为本”,所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此即性情正治的表现,而世俗政治家通常是“以功利为本”的;诗人多为“性情中人”,他们对政治的态度与涉入,多情之所至,“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性之所为,禁不住为公众代言,即是诗人的正治表现。而追逐权势的政治家从事政治活动,通常是考虑各种事功与利害关系,取舍标准则维护党派利益,为此甚至不择手段不惜牺牲一切,这是世俗化的党派政治必然的游戏规则。不妨说,“诗性正治”是以或爱或憎之“性情”而生发的“正治”,“世俗政治”是为“功利”或“权力”而争夺的“政治”。
诗性正治的情感性与道义性,必然区别于世俗政治强制性与胁从性;诗性正治以性情感化人,世俗政治以律令规化人;诗性正治关注人的思想自由,灵魂自由,鼓励人的个性独立与自由创造。世俗政治注重人的行为规范,以人们的服从性为准则,见事不见人,竭力将其纳入统一指令;特别是极权政治,更是常常导致对人性的冷漠、压迫与摧残。
诗性正治是“务虚”的,其本质是精神化的,而非世俗政治“务实”性的物性化操作。诗性正治赤诚坦然,事无不可对人言,它的意图是绝对透明的,这也使它区别于世俗政治的权谋隐秘,谋取党派利益的灰箱暧昧性与铁幕密封性。
如果说,世俗政治只不过停留在社会化层面,以维持社会安稳为要务,只看重形而下的实利效应,诗性正治却以精神性对现实层面的社会文化作更高层次的超越。诗性正治关注的是精神生态(心灵中情感与想象的丰富,意志的自由与潜意识的释放等等)特别是形而上的精神走势,这对于凝聚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塑造一个民族的人文性格,显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诗性思维的想象性与意象性表明,诗人是善于想象的,不像世俗政治条条框框的指令性那么刻板;诗性精神天然倾向理想化,诗性正治力求上升的理想性,亦不同于世俗政治匍匐于实利的务实性。
世俗政治多以权势集团为载体,以党性或派性作为衡量尺度,谋取党派集团利益,常常表现出不容异端的小肚鸡肠,常常为党派私利斗得不可开交。此处姑且不说党性政治中那一种翻云覆雨,必置对方于死地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单单看派性政治就够了。回望03年中国网络诗场“下半身”与“垃圾派”那一场场恶斗吧,许多平时害怕谈政治,闻政治而心惊胆颤的诗人,为派性政治争斗却是何等勇猛,何等投入。“政治”这东西,已使声称远离政治的诗人身陷其中不能自拔。
诗性正治面向平民大众,以人本主义为基础作普泛的人文价值取向,并以道义情怀为终极关怀,捍卫人类共同的利益与尊严,以诗性精神为动力探寻人性的秘密,寻求人性与人权的完美体现。诗性正治以其特有的精神涵量,一方面激烈地试图为世俗政治纠偏,同时亦能够宽宏地理解、包容和化解世俗政治的失误。
可惜的是,一般人匍匐在“务实”的世俗层面,常常轻视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之物,只看重一时显赫的物性化成功,根本不了解精神力量对历史时空的穿透力,不懂得“诗性精神”始终以巨大的容量审视并涵盖“现实”的一切。
作为话语方式的诗性正治
诗性正治在其表现上,是作为一种话语方式显现的。
话语方式针对情感和思想言说书写,作用于人的观念意识。它的功能是促使思想警醒的揭发与批评,而不是落到社会现实层面的具体运作。诗性正治在艺术领域、思想领域和精神领域进行的话语斗争,再激烈也是和平的,非暴力的,决不会毁物害命,因而被称之为“天鹅绒式的***”,“红玫瑰式的***”。但同时,诗性话语对人性的穿透应该说更加深刻,所产生的后果也更加久远。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性正治也是对党派政治社会性运动的超越。
在诗性正治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决不同于党派政治非要划分等级不可。因而在话语表现上,诗性正治以其平等对话性,区别于党派政治的等级独断性。诗性正治是在平面讨论中摊开和发展的,它永远有分歧,有辨难,也永远的多元互动。诗性正治以其平面争论性,区别于党派政治的中心极权性。当然,话语争锋也有其直接性,但其直接针对的仍是心理层面;虽然,话语争端也有其“杀伤力”,但这种“杀伤”或“伤害”不会使身体血肉横飞,更不会对生命造成毁灭。诗性正治的话语之锋再尖锐,话语之争再激烈,也只动口动笔不动手,因而是非暴力的;决不同于党派政治权力之争那种动用刀枪或监禁毒打的暴力性,动辄向对方的肉体生命下手!
只要不限制言论自由,话语方式最容易达到双方或多方的平等与平衡。任何一方都能充分行使自己的话语权来捍卫自己,反击对方。而显然,作为纯粹的话语争斗,也最容易彰显争战双方的真假、高下、雅俗、对错,以理服人与无理取闹等等。如果没有外在压制,诗性正治就永远是生气勃勃的。而党派政治通过集权方式统一个人意见(比如所谓民主集中制),常常导致专权独断,使专制独裁顺理成章,顺势而成。文革时毛式的“最高指示”可谓登峰造极,又如希特勒、萨达姆等等独裁者的专制,莫不如是。
因此,党派政治必定造就两种人:一是专权独断者或专制独裁者,一是服从、屈从乃至胁从的被驱动被奴役者。而诗性正治则造成独立自由的个体人格,奉行“君子不党”原则的诗性正治中人,必然是特立独行并尊重他人之个体人格与独立个性的自由个体。诗性正治包容不同意见,理解不同观点之的多元价值,较易造成宽容的社会氛围。党派政治因其以独断性统领依附性,因此常常党同(或派同)伐异。这里且不说“党同伐异”的“残酷斗争”,在文革的“武斗“中,“***群众”不是分开成了“保皇派”与“造反派”,同样为“保卫毛主席”而大搞残酷与残忍的“派性斗争”么?党派斗争的世俗性反映到中国诗界,不也出现过上世纪末所谓“民间”与“知识分子”两大集团“盘峰之争”的丑剧?网络上“垃圾派”对“下半身”的激烈讨伐?同为垃圾诗人,亦有“垃圾运动”与“垃圾派”之间过激的下流骂战?如此等等,可见党性政治与派性政治极易造成“只许我方放火,不许他方点灯”的独霸作风。试看号称著名诗人伊沙徐江等知识精英主持的《诗江湖》***肆无忌惮地大删批评他们观点的帖子,常常动辄将异议者关进小黑屋,便是这种“派性政治”独霸作风(扩而开去即“党性政治”钳制言论自由,镇压监禁异端人士)的生动注脚。
不过,仅就话语层面观察,争斗再激烈,再无情,论争或骂仗双方的言说无论充满多强烈的暴力色彩,只要停留在话语方式上,而不是棍棒刀枪式的大打出手,其本质上仍然是“非暴力”的。虽然话语争端一旦放开,脏话骂话乃至流言蜚语满天飞,也会使“正人君子”不知所措。其实,真理在手者要骂人也不是不可以,鲁迅骂人的刻毒人所共知。我还发现,凡是大人物都不怕骂,也最敢骂甚至也最会骂。***人的老祖宗恩格斯就曾兴奋地谈起过他们的“下流论战”——
不论马克思,后来他的女儿,以及现在的我,——大家都力求赋予这个论战以愉快的性质……如果在这里也有什么有趣的东西,那可以完全归功于马克思对于他“始终暧昧的人格”的阴暗方面所施加的打击。这些打击是遭受者现在想在事后当作“他的下流论战的粗鄙表现”加以躲避的。伏尔泰、博马舍、彼尔.路易、古里耶的猛烈的论战被他们的论敌们——贵族士官、僧侣、法官、和其他成帮的论敌——叫做“下流论战的粗鄙表现”,可是并不妨碍这些“粗鄙表现”成为众所公认的杰出的典范的文学作品。我们从这些和其他类似的“下流论战”的榜样获得了很多的愉快,以致成百的布棱塔诺也不能把我们诱入德国普遍论战的领域。因为那里只充满着无力的憎恨,微弱的妒忌,和最绝望的苦恼。(《马恩论艺术》第一卷,120页)
当前,中国网络诗歌社区***,下流骂战的情景屡屡出现,看其结果,多半是骂得赢就骂,骂不赢就走,或干脆不理。人们对此已见惯不惊,习以为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表明唯有话语方式能实现对真理的探求。因为仅仅是网络上言论的相对自由,也使得多数诗人具备了对骂人话下流话的免疫力。而且公道在人心,独霸思想在话语论争中要占上风是难以得逞的,我们还没见过没占理只会乱骂者处处得胜的。
诗性正治的话语方式,诗性正治奉行的言说自由,永远是诗人们的正当行为。诗性正治最能实现思想对思想的审察与清理。
诗性之道与政治凌辱
对于历史与社会文化中的政治现象,诗人以诗性之道加以言说,以诗性姿态加以表达是非常自然的。诗人以诗性姿态观察政治,以诗性姿态言说政治,以诗性姿态书写政治,以诗性姿态批判政治,最终以诗性感悟照亮政治,以诗性精神提升政治。我们欣赏诗人这种“诗性正治”的艺术姿态,我们希望诗人们都能坦坦荡荡地直面政治,松松爽爽地关注政治,机机灵灵地点击政治,快快乐乐地谈论政治,开开心心地书写政治,有时也冷不丁犀利尖锐地刺痛政治。如散心的《把俺的屁放在媒体头条新闻》——
从中央到俺
都把“三农”问题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俺脱离了农村却一直心系农民兄弟
屎拉在他们的庄稼地里尿撒在他们的菜园子里
看俺执行政策是否打折扣就看俺的屁放在哪里了
都说菜的营养在汤里文人的价值在屁里
为了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俺请求新闻媒体把俺的屁
都放在头题头条吧
它表明的正是诗性正治写作注重社会意义内涵,充当人类良知与时代证词的人文品质。这是诗与政治最为正当也是最为正常的关系了。
我们提倡“诗性正治”写作,并不意味着主张诗人都把笔锋集中在与权力话语对抗的狭窄空间,这完全没有必要。将广阔的社会文化现象纳入视野,这才是诗性正治的常态。这正是诗性正治的关注“面”与极权政治关注“点”的根本区别。
诗性正治追求的理想境界,是精神高蹈性的形而上的“道”。
真正的诗人对于世俗政治,自有一种心理优势,诗人“成功在别处”,一种来自精神上空的洞见照彻世俗社会的种种病象而使其发出先知之声!歌德、雨果、拜伦、雪莱、裴多菲、普希金、莱蒙托夫、泰戈尔、惠特曼与中国的屈原、杜甫、苏轼、陆游等大诗人莫不如此。他们以诗性正治对所处国度的社会生活,对于人类文明进程所起的巨大影响人所共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如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显赫一时的政治制度,早已成尘作土,而诗人们创造的人类精神智慧,那一盏盏永不熄灭的明灯,依然闪耀在历史的长空。
诗人不仅是时代生活之真善美的发现者和欣赏者,同时也应该是人类社会之假恶丑的感受者与揭发者。诗人对社会生活的感受性较常人敏感得多强烈得多也深刻得多。“天无语使人言之,此乃大诗人之事业。”那么,发自生命的苦痛与良知,为捍卫自我与人类的尊严,诗人不禁要以诗歌话语谴责罪恶抗议暴行——“用语言把人心烧亮!”(普希金)世界诗歌史表明:越是大诗人,越是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寻求人类福祉的激流之中,对现实世界的虚假,对时代风气的腐败与社会生活的丑陋进行不遗余力的揭露与抨击,诗歌对世俗政治实施干预当是天经地义!
然而应该看到,世俗政治却会常常对诗与诗人施以暴力凌辱,这在专制极权体制中犹为突出。中外诗歌史证明,在诗歌写作的头顶常常密布政治迫压的阴云,向诗人震响政治伤害的霹雳!屈原但丁遭流放,普希金被谋杀,引起另一位年轻的诗人莱蒙托夫拍案而起抛出《诗人之死》一诗愤声疾呼,揭露沙皇势力谋害诗人的罪恶。拜伦以诗性正治向世俗政治进行话语对抗,终遭放逐,客死他乡。试看中国隐态诗人哑默以精细的资料对俄罗斯白银时代惨遭摧伤的诗人所作的评述——
迫害、镇压、无情打击和严厉惩处。在他们身上我们处处可以读到枪决、判刑、监禁、未经法律程序的逮捕、秘密审讯、流放、流亡、逼疯、逼死、自杀,被迫改行、停笔,烧毁自己的成果;作品得不到发表或出版,手稿遭查抄,作品被查禁、收缴、销毁;信件被非法邮捡,函件被无理没收,巨著湮沉数十年,文祸延及家人,编辑、编辑部、出版社、报刊杂志以及读者……他们中有布宁、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也娃、曼杰斯坦姆、古米廖夫、勃洛克、布尔加科夫、雷巴科夫、巴别尔、别雷、安德列耶夫、巴尔蒙特、左琴科、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沃隆斯基、普拉东诺夫、纳博科夫、皮利尼亚克、扎米亚京、捷列瓦尔……其人数之多与级别之高——多数俱是一流作家,遭遇之惨真是触目惊心!
——哑默:《疯狂百年——俄罗斯文学悲剧肖像》(民刊《大骚动》第四期)
就在当今中国大陆,亦有无数铁血事例,证实专制政治对诗人的凌辱与迫害:诗人林/昭被无理圈狱直至枪杀;诗人黄/翔为了诗歌而六番入狱;80年代以来,为诗歌坐过牢的又何止周伦佑、廖亦武、杨春光等人;进入新世纪的网络时代,不久前即有诗人师/涛被抓冤判十年,诗人郑/贻/春亦因言论犯禁被抓监/押审/讯;诗人杨春光因屡向极权政治挑战遭***棒击头部,死里逃生留下后遗症,终发脑血栓直至脑溢血英年早逝!……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因国共两党政治迫害遭受摞难中国诗人之量,并不下于俄罗斯!可见,当诗歌写作触及极权者的痛处,小肚鸡肠的政客即会恼羞成怒,专制政治以暴力凌辱诗人与诗歌写作,即成家常便饭。这种极权政治暴力的野蛮,诗人黄翔曾以《野兽》一诗加以感发——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我的年代扑倒我
斜乜着眼睛
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
撕着咬着啃着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此诗写于1968年疯狂文革兽性暴发的高峰期,它揭发了两类兽性:群众专制的与诗人个性中的。区别在于,群体极权性的“专制野兽”是一种现实性社会暴行,能够伤害直至毁灭人的肉体生命;诗人个性中的“野兽”只不过作为一种话语的愤怒表白而已。但是,在独裁者对自由思想严加钳制的极权语境中,诗人通过话语方式的强烈表达,对抗世俗暴力并颠覆反动政治,亦自有其独特的情感震撼性与精神威猛性——
即使我只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年代的咽喉
以诗性精神反击专制暴虐,以诗性话语对抗极权话语,诗人的悲壮已凝重为一座座铁骨丰碑!诗人以话语式的非暴力方式不断消解政治暴力,已成一种宿命!为迎来完全彻底的言论自由时代,必然会有诗歌斗士前赴后继,屡扑屡起……
从文本价值角度看,大凡表达了人类的良知与正义,敢于对现实的政治黑暗进行勇敢批判或为真理讴歌的诗性正治写作,如屈原、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等人的作品,大都能流芳千古。
当代受迫害遭封杀的诗人诗作也不例外,在他们的遗骸上,将滴下后人感激而景仰的热泪。
人们希望今天的诗人们不要仅仅孤芳自赏,不要只是自我抚摸,不要只写那些与民间疾苦无关痛痒的风花雪月,不要对权势腐败视而不见退避龟缩,不要对人类的共同困境以为事不关已漠然置之,它要求诗人热切感应现实社会情绪,积极地应答身处其间的时代精神。
诗性正治与先锋写作
而今的中国诗坛,“性话语”乃至“排泄话语”禁区已经打破,中国诗歌对“性”与“屎尿屁”的书写完全自由无碍了。至于写得好写得坏,就看诗人自己了。在今天享受写性与写屎尿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诗人,难道不该感谢前人冲击这两个禁区的披荆斩棘?现在,中国诗歌面前只剩最后一个“政治话语”禁区了。这块最大最坚稳的政治意识形态禁区长期横亘在当代中国诗人面前,终于因了网络时代的到来开始摇晃。中国诗歌的先锋品格,必将由于正视并敢于冲击这个禁区表现出来,亦将因善于突破这一禁区而愈益彰显出来。比如非非主义提出的“红色写作”、“体制外写作”,便是在理论上具有操作性的反叛极权话语的表现;又如今天网络上的提出的反饰主义写作,争取话语权力写作,俗世此在主义写作等主张,亦是坚持诗人良知与人文精神,奉行韧性抗争的诗性正治表现。
由于极权专控的严酷,“知道分子”们的整体堕落与群体阳萎,期待大规模冲击专制政治禁区的写作在目前还不可能以流派、集团、等有组织的形态出现。换句话说,诗性正治先锋写作的非派别性与非组织性,类似于白蚁式的繁殖。似乎先是以个体觉醒零星地散见,阵歇地闪击,当这种如萤如烛之情与如灯如炬之思闪闪烁烁,以作品传感作品,且随处可见个体在呼应个体时,这种看起来独立的分散的话语策略,对于消解极权话语的一统江湖局面在实质上却是极其有效的。随着这种松散化写作顽强的开展,整一的话语变革局面——“话语换场”终究会形成。因此,诗性正治写作既是性情,更是觉醒。这种个性化的觉醒是渐次完成的,它是一个过程,偶尔为之,率性而为,都无不可,不必要求群体一致。更不必时时处处都是攻击式的写作。像杨春光那样主要从事“后政治”挑战写作的诗人,有几个甚至只要“一个”,也就够了。
当今在中国网络从事诗性正治的先锋诗人,除刚去世的先驱诗人杨春光而外,还有反饰主义的丁友星,争取话语权力的小王子,从事低诗歌运动的花枪,低诗潮的弄潮儿典裘沽酒等人;此外,垃圾诗人徐乡愁、管上、徐慢、丁目、黄土、一空、彭澍、小蝶、散心、老德、蓝蝴蝶紫丁香等人,非垃圾的东海一枭、水古、钱刚、西部快枪、郑小琼等诗人,都有诗性正治力作涉网问世。笔者最近粗略检查了一下,零星地从事过这种诗性正治先锋写作的诗人,竟有好几十人!超过网络上任何一个诗歌流派!理解当今中国诗人面对的时代难题,我们应当耐心地等待诗性正治的先锋写作对诗坛败象的突破。
笔者同时研究了网络上出现的诗歌文本,发现当前的诗性正治写作多以低诗歌的面貌出现,其基本特征就是站在社会底层的平民或贱民立场,以崇低审丑的姿态“以下犯上”。从其表现方式看,低诗歌以“反讽”为中心所创造的“消解式”话语策略尤其值得注意,其诗性艺术逐渐形成了一套不重说理的非理性表现套路(这似乎印证了杨春光“不讲道理”的诗歌写作主张)。比如徐乡愁的悖理反讽,杨春光的谐音错位,典裘沽酒的名人戏仿,管上的底层贱民写真,皮旦的虚拟对峙,凡斯的荒诞影射,小蝶的***示威,浪子的语境颠覆,黄土的情绪嘲骂与事象报露,赵思运对领袖语录的反讽还原,典裘与散心等对伟人言语的调侃俗化,蓝蝴蝶紫丁香对政治残酷性的溯源式冷视,东海一枭放言无忌的嘻笑怒骂……等等。在网络上,低诗歌诗性正治写作创造的话语方式还有转喻、冷嘲、佯谬、双关、亵渎、搞笑、抠像、换位、戏谑、装傻、归谬、复调……等数十种!可见,当今中国诗人为对抗世俗政治的专横与极权意识专制的独断权威话语,有多么广泛而生动的诗性创造。
“诗性正治”与“网络政治”的对接
网络空间对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权力、政府管理、国际关系等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种新型的政治现象:网络民主(又称赛博民主)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网络政治应运而生。
网络政治内涵三个层面:
1、虚拟空间的政治现象——虚拟政治;
2、网络政治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影响;
3、现实政治主体对网络社会能动的反作用。
正在西方各国掀起研究热潮的网络政治,有如下一些特征:一、直接性。公民直接参政议政成为网络政治最突出的表现。二、平等性。指人人在参政议政上的平等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在人与人之间应无差别。在网络上的虚拟平等远比现实社会的实际平等容易实现得多。显然,网络社会更能保障每个人的平等权利。三、便捷性。政治活动在网络上进行的速度与方便有目共睹。四、廉价性。不受时空限制的信息传播的***用大大低于社会现实政治运作的巨额花费。
我们感到,诗性正治与网络政治之间几乎有天然的联系。在当今时代,政治家们与各个政党在运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方面已达到惊人的地步。与此同步的是,在网络社会,愈显增多的网民,分散来自各地的个体,因了共同的兴趣,或对某一特别事务的共同关注,即会迅即发出共同的心声,这一群体之声往往有“一石激荡千层浪”的传感效应!这给真正的民主制和代议制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所谓国家安全,公共事务、言论自由、隐私保护、公民参与,政治选举,官僚机构,贪脏枉法,政治开放等,现实政治的方方面面,都因为互联网的崛起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正在成为专制极权制度的无从抵御的掘墓场!而且对传统的民主政治理念也发出强烈的挑战,其为全球民主的发展必将作出最有力的贡献。
互联网的出现将最终导致集权制等级制的政治形式无法正常维持,最终让位给平面政治与平等政治。这对于天生崇尚个性的诗人,是何等的幸事!例如,垃圾派从成立到如今,不断有诗人零星退出或群体退出,使垃圾派大伤元气,这就迫使作为创派活动与实际掌控的组织者不断调整姿态(愈来愈姿态平等)以维系该派别的成员稳定并注意平等地吸收新人。这例子非常有说服力,表明曾给人搞等级制和偶像崇拜印象的“老头子”在独立思考的诗人面前一筹莫展。最终向平面与平等局面——即权力扁平化和权力分散化屈服。如今,无论是单独退出的诗人,如张玉明、老德、法清等,还是群体退出干脆另外组成“垃圾运动”的诗人,与原垃圾派在实际地位上均处于同一平面,在话语权力上则是完全平等的。而在垃圾派内部,也越来越出现彼此协商分工合作的运行态势,作为《北京评论》总版主的皮旦,与作为垃圾派成果总编撰的徐乡愁已然只出演了某种服务者的角色。这使我们对网络展开政治民主更有信心。
上述例子,只是诗性正治与网络政治在组织形式上对接的表现之一。在当今的网络,诗性正治的多种表现形态都可以在某种角度某种范围切入网络政治,实现两者的焊接。诗性正治与网络政治多方面多角度多渠道的对接,实际上都是话语对接。在种种话语对接中,诗性正治将引导中国先锋诗歌沿着“履行话语职责、争取话语权力,创造优性话语”的方向不断前进,实现话语换场,最终以“公民”话语取代“顺民”话语,创造未来全新的文化景观。
05年8月写
05年10月15日改毕

————
✅生活小常识|✅生活小窍门|✅健康小常识|✅生活小妙招✅情感口述故事